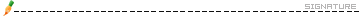在八十年代初,我家建了新房子,当我们搬到新屋时,邻居也就只有两三家,其中一家离我们比较近,加上有那么一点什么亲戚关系,因此也就经常串门。这家邻居是一对老夫妇和好多个儿女,我称呼老夫妇为伯伯和伯母,他们是一对很慈祥的老人,一家人在市场上经营豆制品生意,我有空或者放假时就经常去他们那边帮忙,他们也会给我一点钱买学习用品,因此我很愿意帮他们干一些小活。伯伯和伯母的感情很好,我从来没见他们红过一次脸,也从来没见他们责骂过儿女,他们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所以我很羡慕他们一家。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伯伯家来了一位女人,看起来很美,大概有五、六十岁吧,很有富态、很有气质,我猜她年轻时肯定是个大美人。伯伯刚好在干活,见到她便先停了下来,笑着说:“阿妹,你来啦。”他们简单的寒暄了几句,伯伯便又继续他的工作。他的阿妹就自己坐在凳子上,目不转睛的看着伯伯干活,伯伯的人转到哪儿,阿妹的眼球就跟到哪儿,而伯伯偶尔看到他的阿妹,两个人就都会露出会心的一笑,趁着空闲时就聊上几句,阿妹时不时也会帮伯伯干些简单的工作,显得很自然,很有默契。我当时一头雾水,平时怎么没听他们说有这么一个阿妹啊?做邻居那么久,也没见过伯伯的阿妹来过啊。过了不久,伯母和几个儿女们从市场上回来了,他们见到阿妹,都兴奋得又喊又叫的,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就停下手中的工作先回家了。后来,从伯伯儿子的口中了解到,这个阿妹就是伯伯的干妹妹,住在汕头,有空就会过来探望他们,而他们几个兄弟姐妹有空也会去汕头探望这位姑母,阿妹虽然不是他们的亲姑母,但他们之间的感情比自己的亲姑母还要深。
后来,我又见过阿妹来了好几次,有时也带着她的儿女一起来,每当阿妹他们一来,伯伯家就仿佛过节一样,很热闹。他们一大班人都在家门口,边干活边聊天,而我也难得一见伯伯有这么清闲的时间陪阿妹在门口喝茶、闲谈。阿妹总是笑眯眯地看着伯伯冲茶,他们有时是轻声细语地交谈,有时会发出几声爽朗的笑声,有时又是笑着互相对视,仿佛一切尽在不言中,但大部分都是阿妹在讲,伯伯在听,每当见到这样的情景,我就恨不得我也有这么一个姑母,也就可以像他们那样“过节”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八十年代末。有一天,听说伯伯病倒了,而且很严重,我想到伯伯家去看望,但家里人都不给我进去,也许是我年纪还不是很大吧,也许是大人们有预感伯伯将要离开人世,所以才不让我进去,我就只好傻傻的站在门口。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过我的眼前,直奔伯伯的房间,我知道那肯定是阿妹了。在伯伯病倒的那段时间,我在家门口经常见到阿妹站在墙角偷偷的哭泣,哭完就把眼泪擦干,然后又进去陪伯伯,有时她也会在门口呆呆的站着或坐着,伯伯的孩子们把饭菜盛在碗里拿出来劝她吃,也没见她吃过一口,只是在那儿哀叹和擦眼泪。虽然每个人都希望伯伯能好起来,但最终他还是走了,我想伯伯在临终的那几天,有阿妹陪着,他肯定是开心地走完人生最后的那段路的。阿妹在那几天哭得天昏地暗,喉咙都哭哑了,话都说不出来,她的儿女见她这个样子,吓得不敢离开她半步,不停地劝她、安慰她。
村子里有个习俗,当一个人去世后,大概过三个月左右,家里人就得为去世的人办法事,称为“百日”,“百日”后的第二天,就要请一个巫婆来给去世的人招魂,让已经去世的人和家里人做一次“对话”,“对话”的场面往往是哭声一片,愁云密布。为伯伯招魂的那天,阿妹也不例外,她在和伯伯的“对话”中,哭得一塌糊涂,要不是有人搀扶着,她早就哭倒在地了,阿妹同时还用录音机把整个过程给录了下来。那天过后,我经常见到阿妹一边听录音一边哭,无论是谁,都不许碰那个录音机,她饭也不吃,水也不喝,直到累了、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去,醒了之后又开始听,大家都拿她没办法。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天,最后,阿妹在她儿女和大家的劝说下,还是收拾好录音带和她的儿女回汕头去了。
从那以后,我就在也没见到阿妹了,如果她还健在的话,我想那盘录音带应当就是她今生的最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