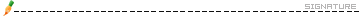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王晓渔(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1975年,一位兵工厂工人和一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相遇。当时前者二十来岁,后者六十有余,但身份和年龄没有构成思想交流的障碍,两人由此开始了三十余年的交往,风雨无阻。老教授是周辅成先生,小青工是赵越胜先生。赵越胜在《燃灯者:忆周辅成》(湖南文艺,2011年9月)里回忆了两人交往的细节,几近完美地实践和示范了“薪火相传”的精神。在我看来,与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辅成尤为推举拉波哀西《自愿奴役论》的观点,要想改变受奴役状态,“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自己不反对自己”,这似乎是一个退无可退的底线,但是在鼓励服从以致盲从的年代,又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需要付出沉重代价。
抗战时期就与唐君毅、牟宗三等朋友创办《理想与文化》杂志,周辅成可谓德高望重,但因为不合时宜,逝世时校方全无表示。赵越胜从兵工厂转入中国社科院工作,创办了在1980年代的北京思想界颇具影响的沙龙,随后去国离乡,从事丝绸生意,阅读与写作再次成为业余爱好。一位“处江湖之远”,另一位“乘桴浮于海”,这或许就是“燃灯者”的命运,但“回也不改其乐”。
读着《燃灯者》,常常想起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那些在黑暗时代依然内心明亮的人们。他们既没有逍遥地“避世”,也没有汲汲于“入世”,而是做一名在场的旁观者。阿伦特在《责任与判断》(陈联营译,上海人民,2011年7月)里这样说:“理解、反思政治而不必是所谓的政治动物,这确实极有可能。”
在《责任与判断》里,阿伦特思考的依然是“黑暗时代,个人何为”的问题。“你为什么参与屠杀?”“我只不过是服从上级的命令。”这种问答常常出现在二战之后的纳粹审判中,也几乎出现在任何一次类似的审判中,比如对红色高棉的审判。但是,“服从”无法作为无罪辩护的辩词。阿伦特指出,向那些参与暴行者提出的问题绝不应该是“你为何服从”,而应该是“你为何支持”,“如果我们能够把‘服从’这个毁灭性的词语从我们的道德和政治思想词汇中剔除,那我们就会受益匪浅……重新获得从前时代被称为人的尊严或光荣的东西”。
阿伦特反对滥用“集体责任”的说法,她认为这是一种虚假感伤,“那乍听起来如此高尚而诱人的‘我们都有罪’的叫喊,实际上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开脱罪行”。
为有罪的人开脱罪行,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骨头里面挑鸡蛋”。俄罗斯作家利季娅回忆,1960年代中期报上直接或间接地肯定斯大林的地方越来越多,对此诗人阿赫玛托娃评论道,“这就像,承认他是吃人的恶魔,但口琴吹得好。”
利季娅曾被开除出苏联作协。《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蓝英年、徐振亚译,广西师大,2011年9月)不仅收入了她的《被作协开除记》,还收入了这位女作家对萨哈罗夫等的回忆,以及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的日记,这也是苏联时期的“燃灯者”名单。有些遗憾的是,利季娅的文论未能收入,比如书中提到的《不是处决,而是思想,而是言论》。
“燃灯者”并不总是遥远的。张立宪主持修复的《共和国教科书》(新星,2011年9月)就是一盏触手可及的灯火。民国教科书,这两三年一时纸贵,但是我对时下评价很高的《开明国语课本》一直保留看法。《开明国语课本》出版于1930年代,当时国民政府建立党国体制,这套教材已有党化教育的痕迹,只是痕迹不算触目惊心。
相比之下,我更偏爱民国初年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那是公民教育读本,可惜此前只能在网上读到只言片语。虽然很多出版社加入翻印民国教科书行列,却聚焦于国文科目,而且常有改动。看到张立宪主持修复的《共和国教科书》,有叹为观止之感,不仅收入了“新国文”和“新修身”,还将“教科书”和“教授法”一网打尽,同时还收入了一册《公民须知》,可谓竭泽而渔。整套书按照当年的版式制成线装书,缺点是太过完美,以至于不忍触摸,唯恐污损。如果条件许可,似乎可以买两套,一套“远观”,一套“亵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