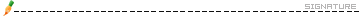季羡林先生的良知底色、人格与境界
(作者不详)
98岁的季羡林先生在301医院辞世的时候:7月11日上午9时,我正面对《原上草》审读油印本的《广场》,即一九五七《北大民主墙选辑》。那自然只是《广场》的复印件:已是孤本的原件,流落珍藏在巴黎郊区塞纳河畔的林希翎女士处。那天,沉疴在身的林大姐特地从巴黎平民医院溜了出来,随一位巴黎友人出现在一家复印店。大姐后来在越洋电话里向我感叹当时的心情时,依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终于赶在五四九十周年前夕,让《广场》回归了故国,回归了北大故人!……..
其实,这也就是我此时此刻对魂天而去的季羡林先生的感念与敬意啊,或者说,正是在林希翎感叹的境界里,我面对着季羡林先生背影令世人瞩目的高度,他良知的底色,……
是的,在我固有的精神视野里,原来并不知道季先生是20年前5.24“首知联”四十余位发起人之一与坦然的担当者,但世纪末季先生催生的“思亿文丛——岁月文丛“却于我印象极深。特别是《原上草》、《六月雪》系列,在我看来,就是记忆、反思中国的世纪高度了。因为又过去近十年:强迫遗忘的十年,精神滑坡的十年,面对盛世总理五次探望的季先生自己也竟自慰于“假话绝不说、真话不全说”的十年,近十年前那系列思忆的精神奇观,依然为当代出版界难以企及与复制。而无论是当年荟萃于《广场》的《原上草》,还是岁月文丛,它们之得以在北大百年前后面世,据说季羡林先生都与有力焉:按钱理群先生的说法,没有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季先生,也许《北京大学言论汇集1957》未必能从北大档案馆里岀得来,那么,《原上草》也就有可能至今还沉压在遗忘的冰山之下吧?至于《没情节的故事》、《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等岁月文丛系列呢,就是时届90的季先生亲任主编的了。也就是说,虽非林希翎珍藏的《广场》真迹,却比广场更广茅的《原上草》之类——这些北大精神传续与弘扬里程碑式的记录,这些新五四——五一九星汉灿烂的见证,这些比季先生独自的《牛棚杂忆》恢宏得多的历史备忘录,都是季羡林推动或主编出版的!
岁月文丛卷首语,就是季先生拳拳的心:
“几十年过去了,回忆往昔岁月,依然历历在目。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老年知识分子生经忧患,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政治运动中,被戴上许多离奇荒诞匪夷所思的帽子。磕磕碰碰,道路并不平坦。他们在风浪中经受了磨练,抱着一种更宽厚、更仁爱的心胸看待生活,更愿讲真话。”
在记录自己“文革”惨历的《牛棚杂忆》中,季先生更披露出他拥紧劫难思忆的忧衷: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教训,也就无法让它真正成为过去。他几乎是大声疾呼:
“‘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
这样的季先生作为北大副校长,对光荣与耻辱并存的北大之扬弃,该算是有所作为的;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其人文瞩目得也很是地方。何况季先生人生暮色里还有十分灿然的一抹:力辞“国学大师”、“国宝”、“学术泰斗”的赐谥。这曾得到李敖的认同与力挺。可李敖立论所主要秉持的,似不在“梵学并非国学”,而在于: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直面时代苦难,应该担当国家核心问题所赋予的使命;真正的大师,尤该以这样的姿态引领时代。李敖质疑:以大陆的政治惯性与文化生态,是很难诞生这样的大师的,尤其对于季羡林先生与巴金老人这类生性柔弱的文人,更难此求。
这样具论到季先生,李敖先生所论,看来就又对又不对了——
也许应该说,文弱一生、妻儿一世、终生不解胡适“陷入”学术研究与政治社会活动“怪圈”的季羡林先生,能在梵巴文的象牙塔里独守清高,能在中国的牛棚里翻译古印度长诗,也能在盛世主编《东方文化集成》、总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却确乎既不敢像清华老同学胡乔木那样投身救亡,也不敢直面留德十年异国女郎的爱情,更不敢林希翎式叱咤维权乃至引领五七,甚至文革后虽有心《牛棚杂忆》,亦无胆直斥罪魁,惹得聂老佛爷满心不快,纠缠不休……也确实,生命最后这些年的季先生,几乎连书房都搬进了301,一如巴金最后十年全几乎以华东医院为家,大国总理六探的殊荣甚至为巴金所未有。而这殊荣的深处,分明正是世纪老人们的柔弱对于权势盛邦的可饰性——盛世聚焦的特护病床上:巴老沉默地跨越百年无疑是一种装饰;季老疏离之外的和谐之崇、孔孟之尊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之滔滔,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装饰?……然而,我还是不能全然苟同李敖,因为毕竟精神中国皆知:正如巴老首倡文革博物馆,季羡林先生在20年前的疾呼与担当之后,还以推动出版《原上草》系列与主编岁月文丛的方式,真诚而执着地直面过时代苦难,分担过对国家核心困窘的呼唤与回答。凭此,我甚至不无遐想:如若不是季老年复一年三〇一,博雅塔下的地气未必不会再次拂亮这位世纪老人良知的底色,幸运之间,那部88个北大校友的《梦萦未名湖》也许不删林昭就出版了吧?
季先生所幸的是,他良知的底色曾有充分的条件得以呈现;而不幸在于这种呈现往往又因权势的恩宠所暗淡。把那一声“真话不全讲”放大为先生的人格形象,是不公正的——笔者也曾参与这种不公正放大。这应该主要是犬儒时代的悲剧与不幸,尽管终生不解胡适“陷入”学术研究与政治社会活动“怪圈”,恰恰也反映出的季羡林先生某种并非人格的缺陷——一个终生浸淫在东方学偏远学问者对公共知识分子身份与真正使命的不理解。
是的,不是关乎时代走向的穿透与引领者,不是大勇,不是决绝,不是大自由之思想、独立之大人格,不是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甚至也没有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那样的即时寄托与隐晦渲泄:季羡林先生完全不是他的象牙塔之外的大师——尤其不是直面民族国家核心需要孜孜以求的人文国学大师。但权势对他的赐谥与赎买,是权势的自饰。诚实端方的季先生以清醒的力却,持续直面时代的担当,与权势及世俗保持了一定距离,保持了余秋雨大师者流绝无的良知底色。尽管对于我,季先生价值归趋仍颇混沌,但他灵魂的姿态,清晰展示出他的良知在疏离着什么、在趋近着什么……
这就够了,尽管毋须讳言,写着《林昭与索尔仁尼琴弥留时分》的那天,我为季羡林先生遗憾过。今天我想说、我要大声说、恰也正经验着的是:
我惊欣过、见证着季羡林先生直面时代饥渴的承载或担当……它们毕竟属于一种良知的底色。一种人格,一种境界。
这样的季老,去的一定是天堂!
这样的心情,等待着十九日八宝山送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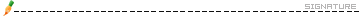
本编辑在本论坛所发大多为转帖,转帖不代表本坛意见。本坛倡导尊重作者署名权。如难以查明作者,只能注明“作者不详”或注明稿件来源,请见谅。本坛对抄袭深恶痛绝,请大家转帖时学习本编辑做法,并且不要转帖那些声明不许转帖的。本坛特别欢迎原创。谢谢阅读和跟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