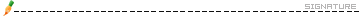童年时候,我十分喜欢玉米不断变幻的颜色:一粒粒饱满的种子泛着金黄,一株株挺拔的玉米棵儿盎然碧绿,一个个浑圆结实的棒子包裹着浓绿散尽的洁白。那时我就想,颜色变化的过程,其实就是生命成长的过程啊。
那年种玉米的时候,我学会了挑水。日子干燥得让人心烦,再不下雨眼看就过了播种的时节。老少爷们儿很无奈,只好带上种子、挑子、水桶等家什儿奔向田间地头。父亲叫上姐和我,也去种玉米。大姐、二姐干地里的活都是把好手。父亲常说姐姐干什么像什么,嫌我往坑里浇水都洒在外边。那年我虽然才有十三、四岁,可个子已经老高了。为对我施以“惩罚”,父亲便让跟着去挑水。他从深井里拔上来两桶水,然后把挑子放在我肩上,一端钩起一个满满的水桶。按照父亲说的要点,我气吸丹田,扎稳下盘,使劲站起。父亲跟在我后面,边走边指点:“屏住气,别泄了劲!”当终于一步三摇地走过300多米路程的时候,我早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父亲扒开我的衣领,肩上已是一片殷红。看着我狼狈的样子,父亲脸上却溢满了笑容。
在耕好、整平的地里,二姐微弓着腰,用镢头刨出一连串的小坑。我懂得了珍惜,小心把每瓢水浇进去。然后,准确地投放两三粒种子,再用脚把周围的泥土轻轻拥上。我喜欢随父亲下地,喜欢一遍遍地重复这个简单的动作。记得当时,我还恍然大悟似地问父亲:“爸,这一个个小坑,不就是一个个待孕的母腹吗?”听了我很“有学问”的比方,父亲点了点头。
正是玉米抽穗开花的时候,我和父亲在地头等待2公里外南山水库的来水。玉米棵儿比白天稍稍精神了些,可还是无精打采。夜,静得出奇。我耳尖,首先听到了水来的声音。看着水哗哗流进地里,父亲赶忙让我到地那头去看水,还叮嘱水快到地头时要喊一声。
我便一头扎进玉米地里。在水流的一侧,用手电筒照着水缓慢前行的脚步。灯光照水,水耀青光。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土地开怀畅饮的声音,微细,却很真切,伴着虫子的鸣叫。过水的地方,霎那间好像有了抽节的声响,有了灌浆的动静儿。再往前走,衣服与玉米棵碰撞发出“哗哗啦啦”的声音。抬头看天,若隐若现地有了几颗星星。周围,还是一片被夜色染黑的浓浓的绿。
每过一会儿,父亲就喊我一声:“快到地头了吧?”我大声回答:“快了,快了。”父亲喊话的目的并不完全在水,还有帮我驱逐恐惧的意思。等到水真的快到了,我便急促地喊:“改吧,改吧!”声音打破了夜的宁静和安祥,在空旷的夜空中飞舞。我仿佛看到了蹲在地头上吸烟的父亲。他慌忙站起,三两锨把水引开。
当十八沟玉米全部解渴的时候,天大亮了。疲惫仿佛突然而至,父亲叫我收拾家伙赶紧回家。下午醒来后我才发现,脸上、手上竟多了几道轻微的血痕。
掰玉米的活儿我没赶上过。只记得中秋以后,玉米堆在家里一像座小山。母亲急活儿,招呼全家老小齐上阵。嗅着玉米棒儿散发出的清香,我慢慢地剥掉一层层薄皮儿,静静地欣赏它那白里透黄的芳容。每当这个时候,我常留上一两片最贴近玉米身体的软柔轻纱,用来遮掩它含羞的笑靥。扒上几个,就把它们辫在一起,成一小嘟喽。碰上几个手能掐破、嫩嫩的小棒儿,就把它们放进锅里,煮熟,当作夜宵。
我常常怀念那些美好的夜晚。在宽大的院子里,明亮的灯光下,父亲、母亲带着大大小小的六个孩子,围着一大堆玉米,轻轻地说着,笑着,唱着。谁渴了,就从茶壶里倒碗水喝,尽管茶叶早就泡掉了颜色;谁饿了,就从锅里捞一个煮熟的鲜嫩棒子;谁想睡,大家都取笑他(她)。等到玉兔西落、眼皮沉重的时候,母亲才准许我们休息。
天刚蒙蒙亮,父亲、母亲的忙碌就打碎了我们的美梦。我们搓把脸,打个舒身,犟打起精神,再把所有的玉米递到支起的木杆、树杈或平房上,让它们安然地享受就要到来的温暖阳光。那个时节,无论你走进哪一家,都会看到悬挂满院的簇簇金黄,都会看到尽管疲惫却洋溢着愉悦的张张笑脸,都会强烈地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殷实和吉祥。
然后就是漫长的寒冬的夜晚了。那时没有机器,邻居大娘、嫂子常到我家喝茶、拉呱儿,还帮着磕玉米粒儿。她们用螺丝刀近乎残忍地在棒子上挑开一条道路,然后用大拇指柔和地让一个个幼小的孩子脱离母体。不大一会儿,双膝托着的簸箕里,已满是散落的颗粒。母亲把最完好、最饱满晶莹的那些精心挑选出来,留作种子,期待着新的丰收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