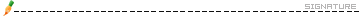为什么赞同“师道尊严”
邵建
不是因为我的职业是教师,我才赞同师道尊严,因为这是一种自然伦理和文化伦理,是一种“序”。
北京海淀区艺术职业学校“辱师门”的视频曝光后,上周的《南方周末》以“全纪录”的方式再现了事件过程,并从“师道尊严”的角度对此展开讨论。事件本身已经无需重复。但,有必要指出,这样的事件可以发生在20世纪,却很难想象会发生在20世纪以前。转从空间角度,它可以发生在传统文化受到根基性破坏的地方,比如中国大陆,却不太容易发生在依然受传统文化浸染的地方,比如台湾和新加坡。这意味着什么?传统毕竟是一种有正面意义的价值资源,如果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是不可能发生“辱师”事件的话;那么,从师生关系的维度修复我们被破坏殆尽的文化传统,就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教育任务之一。
“师道尊严”已经是一个久违的词了,它出自《礼记·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个意思说白了就是敬学者的“尊师重道”。在一个敬学者那里,尊师必然重道,重道必然尊师。师的作用,如果像韩愈所说,是“传道、授业、解惑”,那么,学生又有什么理由不尊重师长呢?所谓师长,是指他的自然年龄、文化阅历、学识修养都在你前面,都长于你。如果你此时又从学于他,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尊师重道就是学生方面的伦理准则,这很自然。像上述辱师情况的发生,不仅反文化,而且反自然。
与其追究这几个学生的文化反常,不如追究这种反常在20世纪的文化渊源。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有功有祸。祸不仅在于从文化上全盘反传统,而且在所谓新文化上鱼龙混杂,引进了包括无政府在内以及与其颇为近通的那些最坏的主义和思潮。它们“斗”字当头,“破”字为务,以各种诱惑人的名义,比如维新、革命、进步等,试图铲除一切既有的价值,以及作为社会维系的文化伦常和自然伦常。这些东西因其名头的崭新,特别能吸引具有反叛心态的年轻人。包括师道尊严在内的传统文化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了自己的厄运,至今还未结束。上世纪20年代,北京学界发生过“女师大风潮”,风潮中的女学生飒爽英姿、斗志昂扬,居然能给校长室贴上封条,非但不许校长入内,还把里面的东西扔出来。上世纪30年代,胡适身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学生集会时,胡适登台发言,下面学生嘘声一片,试图轰其下场(当然胡适也没客气,斥其“下流”,声称有话就上来好好说)。更有甚者,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一些“进步学生”因怀疑清华教务长潘光旦提供学生名单给当局抓人,把他包围起来。潘光旦因年轻踢球受伤而截肢,是个平时离不开双拐的人。可是这一次,学生有意夺去其双拐,头发凌乱的他,只好用一条腿边站边跳,保持平衡,而学生却在一旁围观。这是一种羞辱,对师长的羞辱。别说师道尊严,连人道尊严也没有了。
当然,今天出现的这一幕只是一出闹剧。闹剧也好,像以上以各种堂皇的名义也罢,总之,在传统文化缺失的地方,辱师之类的情形就会有出现的可能。我并非全盘性肯定传统文化,但像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某种外来的文化无条件地否定传统文化,肯定为害不浅。试想,一个接受过儒家“弟子规”规训的学生,会做出那些违反伦常的举止吗?这正是传统文化的正面意义。在今天的学校教育中,适当地有选择地进行一些儒文化的教育,在我看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它未必不比那些现行的政治课更重要。至少在校园里首先就要倡导“师道尊严”,并要让它成为校园中师生关系的一个基本秩序。
在《南方周末》上,有学者认为刻下学校中的现实完全相反,不是没有师道尊严,而是“师道过于尊严”,“学生权利很少被关注”。其实,师道尊严和学生权利无关,这是两个不同质的问题,不该此消彼长,因果纠缠。师道尊严并不必然意味教师侵犯学生的权利,就像没有师道尊严学生权利未必一定受到关注。在校方、教师和学生三者的关系上,其情形往往是既缺乏师道尊严,又缺乏对学生权利的尊重。这才是今日校园中令人堪忧的地方。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