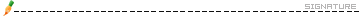契娘
南方周末
□(福建)曹庚长
不知从我几岁开始,母亲为我认了一位契娘——这是老家对干娘的称呼。这位契娘可不是一个寻常人,她是乞丐!不过,她从不蓬头垢面,也不衣衫褴褛。头上挽个圆圆的发髻,穿一身斜纹粗布大襟黑衣衫,30来岁,高挑的身材。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侯开始,更不知为什么,我的这位契娘从隔邻的上杭县流落到本乡来。好在家乡素来都把乞丐看作是来讨饭食的客人,没人欺负她,大伙叫她“讨食客”;我们家则称呼她“上杭娘”——因为父亲母亲早已给我取了“上杭仔”作乳名。
父亲母亲给我找契娘是希望体质较弱的我,自幼就像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乞讨人一样命硬,好养、好带。正是这样,才为我认了一个讨食客来做干娘———这是好多年以后我长大了才明白的。
乡村每5天赶一次集市的时侯,契娘就会带上东西来看我。如果不是她手中总握着一根打狗棍,谁也难辨她是一个讨食客。
契娘总是在近晌午的时分才来到我家。门外首先响起一阵狗吠声,大哥二哥眼尖,争相喊:“上杭娘来了!”母亲立刻放下手中的活,把这位怯生生地立在门外的契娘迎进屋里来。
每一次我都看见契娘给我带来的相同的三件礼物:一件是装在竹筒里给我洗澡用的山泉水;另一件是三五块广饼;还有一件是一小碗四处讨来的“百家米”。她先是望望我,然后一边牵着我的小手,说着我们听不懂的外乡话,一边把广饼递给我们。哥哥和我都嫌广饼不好吃,不想要。母亲却一一把东西接下来。之后,拿过契娘的布袋,满满地装好一袋子白米,再找来几片翠绿的芋荷叶,实实地裹着几大块熟肉;父亲则咕噜噜地给空竹筒灌上自家酿的香醇的米酒,还用芦箕芯像串上羊肉串似的,串上好几挂也是自家制作的金黄色的油炸香豆腐。而这时,契娘正在给我烧洗澡水,烧好了洗澡水后,她一边帮着母亲给我洗澡,嘴里一边喃喃地说着话,可能是菩萨保佑、吉祥平安之类的。洗完澡后,母亲帮她整理好东西,然后送她到门外。这时,契娘的打狗棍已经变成小扁担了。
这样过了一年多,我的身体也渐渐地结实起来了。同时却发现,契娘来我家的次数渐渐少了,后来就再也没有来了。有时侯,听到门外响起狗吠声,我以为契娘来了,可出门一看,看到的是陌生的、脏兮兮的“讨食客”。小伙伴们有时会恶作剧,故意唆使狗狂吠着,母亲便急匆匆地放下手中的活出门吆喝住,同时对我说:“上杭仔啊,问他要什么?”母亲没空闲,便吩咐我们。我说,他不要饭,要大米。“那就快去量一‘米筒’白米打发他呀!”母亲边忙活着边喃喃自语地说:“讨食客、讨食客,落难之人也是客啊!”听了母亲的话,我们从小也学会了善待他们,不论是残的、脏的,老的、少的,我的哥哥和弟弟们从来没有怠慢过一个讨食客。
然而,往来的乞讨人中我却总也不见我的契娘,日子久了我心中便有点惆怅起来。我便问母亲为什么不见我的契娘?母亲对我说:你契娘已经“入了人家”(我们这一带叫出嫁为“入了人家”,即有人娶了她)。
记得那天我听到母亲这样一说,竟然哭了起来。
后来母亲对我说,有人曾见过我的契娘,说她已经有了儿女,日子过得还和顺。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契娘的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