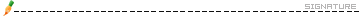奶奶家是放船的船东.奶奶貌美,擅女红.嫁了个商人,没出门做过事.解放,收走了京津两地的洋楼.在伙计们住的胡同里分了最大的一间屋,之后这成了我脑海中的奶奶家.伙计们成了之后几十年的邻居.爷爷去世后,奶奶住我家楼房.旧房子在城中旺地,最早给推平了盖商业中心.邻居们也分散在城中各处.
一段时间爸爸出差,家里只有我们三个女人.一天晚上妈妈等奶奶睡了拉我说话:昨天半夜你奶奶喊得吓人,听不清楚说什么,声音出奇的大,吓得我想去你屋里找你,下了床,就走不动了.吓得我,一个晚上没睡."我还是个小孩子,睡得沉,什么也听不见.之后有天下午,坐奶奶床边说话儿.她老人家自己和我说了:"晚上梦见你爷爷,抓去给人家游街,拿那么粗的绳子系了疙瘩打他.我找他奶奶说理去了,这大小子是我和他奶奶一起带大的,老邻居了,他为得什么呢?棉裤的一条腿还是我帮絮的棉花.这么小,就打人.你爷爷老实人啊!他怕啊!"慢慢的念叨着,奶奶眼里有了泪水.用手捂着脸,很久不说话.这样的梦她做了好多次.
六姨是妈妈的姨表姐,家境不好,小时候寄养在我姥姥家.后嫁了个名角儿家的少爷,一直念叨这少爷是大老婆生的.某年和六姨在广东过年,表姐们去香港,家里只有两个人.半夜里也听见六姨喊起来,声音凄厉,似乎在说什么,又全听不清.我想起来过去问问,腿用不上力气,直直得躺了三个钟,天光放亮才能坐起来.午饭后问起六姨,她回说:"噢你听见啦!我又做那个梦.一家人都四合院中间站一排,一个人拿着宽皮带挨个狠抽.旁边一群人搬着家具只管往院门外的卡车上扔,上好的红木家具,全糟践了.值点钱的小碗花瓶儿,偷的偷碎的碎,全没了."我一直猜想六姨梦里喊的是什么?六姨美,嫁得个阔家公子,中年离异,提起爱情总是愤愤然:"爱情是什么?爱情那就是个屁!"我想她这一生最值得留恋的只是那些瓷器碗儿了.
这之后我翻阅了好多关于文革的书和报告文学,<江青传>看过两个版本,还是体会不出这样的恐惧感是怎么产生的.两个七八十岁的女人晚年经常的噩梦里竟都是这个年代的记忆.
妈妈一直生活得安逸,没受过什么委屈,是当年少见的女大学生,被外公宠得什么似的.她对文革的叙述只一个故事:"你爸爸出差了,咱家冷得能结冰(她老人家不擅长生炉子,喜欢打哆嗦取暖),下班回家一看,毛巾冻冰棍了.单位女干部来咱家动员我下乡,我就是不去,大不了回你外公家去,不上班能怎么样.你猜女干部看见那毛巾之后劝我一句什么?她说有困难就想想雷锋同志.哈哈哈!"妈妈每次说到这里就大笑.妈妈很感激文革,因为同是黑五类,她遇见了呵护她一生的爸爸,有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儿,本来他们是想培养出一个闺秀的,呵呵.我就是妈妈这一生唯一的噩梦.
(妈妈的一通电话闹的,写了这么多.加班,太晚回家了,妈妈找不到我,着急了.想起奶奶等我放学,写几笔记下今天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