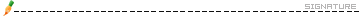工会原来很值钱
吴思博客
一、工会的货币价值
从1927年起,中兴煤矿工人的工资陡然上升。
中兴煤矿位于山东枣庄,当时在中国排第三,产量仅次于日资的抚顺煤矿和中英合资的开滦煤矿。据《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提供的数字,1917年-1926年,中兴煤矿井下工人的平均月薪一直徘徊在7.8块银圆左右。按1比35折算为2003年左右的人民币,相当于273元。那时候,多数工人只有一套破衣服,每天吃两顿饭,高粱面或麦子面煎饼卷大葱,外加咸菜和糊涂汤[2]。用现在讨论农民工问题的话说:井下工人的工资水平长期偏低,增长缓慢,国内需求严重不足。
可是,从1927年开始,井下工人的工资连增五年。到1931年,平均月薪已达13.0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按1比30折算为2003年左右的人民币[3],约等于391元,涨幅高达43%。调查者施裕寿、刘心铨写道:“近年来工资之所以特别上涨,大半是工会的力量。”
调查者抄录的工会与资方的第三次协定可以证明这个说法。协定共15条,第一条就是增加工资。自1930年12月1日起,各级工资平均增加15%左右。随后是关于抚恤金、救济金、假日工资、花红(奖金)摊派、工人浴室、退休金、工作时间等方面的内容,条条关系到工人的切身利益。这份协定,是工人凭借集体力量与公司反复“交涉”的结果。
读到这里,我如受电击,想起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他把贫困理解为权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说得更形象点,他将贫困看作一个健康人被种种法规堵住嘴、蒙上眼、捆住手脚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兴煤矿工人工资的提高,来自一项政治权利的获得,或者说一条禁令的松动:工人有了联合起来与老板讨价还价的权利,有了组建工会的权利。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项政治权利原来是很值钱的。
组织工会的权利可以换算为多少钱呢?调查者说,工资上涨大半靠工会的力量,倘若将“大半”算作75%,那么,工会能给井下工人带来32%的工资涨幅。
这是一条引人遐想的结论。
现在中国约有两亿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约为667元[4]。假如农民工有权利组建工会,倘若这些工会真能发挥在枣庄煤矿的作用,将工资提升32%,农民工的收入就会走出长期停滞,提高至每月880元。全国农民工的总收入将因此每年增加5123亿元。
中共中央在2004年推出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大政策,为中国农民减掉了每年1265亿元负担。如果再进一步,像农村改革之初面对大包干那样说几句“可以可以也可以”,落实一项公民的政治权利,对农民来说,其价值竟相当于取消农业税的4倍。更进一步想,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是否可能从此进入良性循环?国外工会的抵制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是否可能因此减轻?综合动态地计算起来,其价值每年何止五千亿人民币。
二、工会真是工人的命
我关注煤矿工人的收入,本想看看他们对高死亡率的补偿要求在工资上如何体现。结果大出意料。1926年前后,中兴煤矿井下工人的工资,普遍低于盐场、纱厂、面粉厂和铁路的低风险粗杂工的工资[5]。可是,在中兴煤矿50多年的历史上,平均每年有13.5人死于井下事故,年均死亡率约为3.9‰。2003年,中国煤矿井下工人死亡率大概也是3.9‰,与此相应,煤矿工人的工资就比建筑工人的工资多出20%以上[6]。
经过工会的五年活动,中兴煤矿工人平均工资的绝对值提高了6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有43%的涨幅,与其他低风险行业的重体力劳动比起来,高出20%左右,大体说得过去了。
据此可推出另一种计算,以生命为本位的计算:在中兴煤矿,工会的存在,可以补偿每年3.9‰的死亡率,抵得上每年13.5条人命。如果工会被封杀,这13.5条人命,或3471个井下工人每年3.9‰的生命,就被无偿剥夺了。工会果然可以算作工人的命。
1915年之前,中兴煤矿的井下工人死于事故,抚恤金约为70大洋,大概相当于2003年前后的3500元人民币。1927年工会成立后,抚恤金当年就提高到100元,1931年又提高到200元[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工人的命价升值将近一倍,超过了43%的工资升幅。这就是说,工人的生命得到了较多的尊重。
那么,在工会成立之前,在工人性命特别便宜的时候,谁占了他们的便宜?凭什么可以占他们的便宜?这块便宜的实质又是什么?从政治权利的角度看,占便宜的是资本和官家的联盟,凭借的主要手段是限制结社的法令,利用法规占到的便宜属于“法酬”,实质就是血酬——暴力带来的收益。
总之,工会既值钱又值命。政治权利,不仅可以换算为财产权利,换算为钱,还可以换算为人身权利,换算为命。这些权利在效用上是相通的。权利的增加致使工人全面升值。
三、工会成全了工人
据说,在工会成立前,工人的一条命还不如一条驴值钱[8]。1922年,李立三和刘少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也喊过一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口号难免夸张,但思路很让人动心。牛马驴骡之类的役畜,究竟与工人有什么不同呢?
无论是牛马还是工人,都要干活吃饭,卖苦力换取“生存权”,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法律既禁止杀工人,又禁止随便杀役畜,也无根本性的不同。万一出了死亡事故,役畜的使用者要向所有者赔偿损失,资本家则向工人家庭赔偿损失,方式和价格也差不多。
工人与役畜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人有人身自由,有签定契约的自由,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有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如果剥夺了这些权利,工人就不是工人,而是会说话的牲口。用上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概念来说,就是“奴工”[9]。对应“农奴”的构词法,也可以叫“工奴”。
工人不是可以随便叫的。如今的用法来自欧洲,所指的社会集团是那里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在古汉语中,“工人”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不同,并不特指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他可能给地主扛长工或打短工,也可能是“士农工商”中有固定的户籍、技能、义务和生产资料的工匠。在与平民雇主的关系中,他们被称为“雇工人”;在与官府的劳役关系中,他们被称为工役、工夫或工徒;在社会分工和官民划分中,他们被称为工匠或工民。
中兴煤矿的工人,尤其是包工头招来的“外工”,其地位处于工奴和马克思谈论的工人之间。他们依附于“封建把头”,选择自由受到江湖行规等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人身自由也打了折扣。那些直接受雇于公司的“里工”,虽有签定契约的自由,却没有联合起来讨价还价的权利,另找饭碗又难,选择自由便大打折扣。发明“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欧美人,称这种中国劳动者为“苦力”。苦力是工奴和工人的混合体,即社会政治权利残缺不全的工人。
如此说来,工会不仅尊重了工人在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也成全了他们在社会意义上的生命。有了工会,中国苦力就成为工人了。
四、国民党员的贡献
工人的政治权利并不是白来的,行使起来也不容易。
《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说,中兴煤矿的工会,1926年之前开始酝酿,1927年北伐军到达后公开成立。工会最初的领导者,“思想均甚偏激”,经常闹出各种纠纷。
当时的工会也不止一个。1928年夏,国民党中央派周学昌到煤矿整顿,统一组织,规范训练。几个月后,中兴煤矿的事务改由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管辖,省党部另派颜学回(国民党左派人士)等人接管工会工作。据说,颜学回等人利用工会,“煽惑”工人与资方对抗,“离间挑拨”,居心叵测。1929年12月,国民党中央下令通缉颜学回,中兴煤矿的工会事务,由省党部另派邱瑞荃等人负责。
然而,邱瑞荃等人的作为,也和颜学回差不多,不久即因“言动乖张” 被上司撤职。
邱瑞荃等人走后,省党部又派来汪大经和阎玉成等人主持工会工作。没想到,这两位“煽惑”工人闹事的能力比颜学回和邱瑞荃更强。于是,资方搜集他们的材料,向国民党中央报告,中央认为汪大经等人“反动有据”,特派李崇诗(后出任军统局上海站少将站长)到中兴煤矿,将汪大经等人押解至京。整顿工会的事务改派张剑白等人负责。
1930年12月,“山东枣庄矿区工会”奉国民党中央的命令正式成立。折腾了好几年的工会终于进入“正轨”。
工会与资方交涉数年,先后达成三次协议。第一次在1929年2月,第二次在同年8月,第三次在1931年3月。前两次,由于工会尚未正式成立,工会内部有很多问题,公司领导层又忙于改组,协议的各项条件多数未能实行。1930年12月工会正式成立后,一方面努力促成前两次协定的实施,另一方面,在1931年3月与资方代表及山东农矿厅驻矿监理、省党部、县政府、县党部代表达成15条新协定,即前边提到的有关增加工资和抚恤金等内容的协议。[10]
——由此可见,工会的大部分成绩,竟是在未获得合法认可的处境中取得的。国民党派来的颜学回、邱瑞荃、汪大经和阎玉成四位,为了工人的利益,前赴后继,得罪了资方和国民党中央,被视为“言动乖张”,“反动有据”,先后被通缉、撤职或押解至京。在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利、争取政治权利合法化、为工人阶级提供政治权利的实现途径等方面,这些国民党员功不可没。
五、***员的血汗
工会酝酿开创之初,那些被称为“思想偏激”的人,为争取工人的政治权利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2006年3月1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永远的丰碑”栏目,播出了枣庄煤矿七月大罢工的组织者田位东的故事。顺着这条线索,我在互联网上查到一批***人的活动。
纪子瑞,中兴煤矿工会的首创者,1895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县里岔镇里岔村。1924年经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成为青岛四方机车厂第一批入党的7名党员之一。1926年春,受中共山东省委派谴,纪子瑞到枣庄煤矿区开展工运和建党工作。他和工人一起下井掘煤,一起食宿,启发矿工的觉悟,号召他们组织起来,加入工会。
1926年夏,纪子瑞发展了张福林等19名党员,成立了枣庄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不久,又在枣庄中兴煤矿建立秘密工会,发展会员50余名。
1927年6月,北伐军到达鲁南地区,纪子瑞利用有利时机,秘密召集30余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决定公开打出‘枣庄矿工劳工会’的旗号。当夜分工串联,次日便召开了2000余名矿工参加的控诉大会。台上是张福林、梁棠等人的血泪控诉;台下口号声此起彼伏。会上,资方代理人、厂方副经理胡希林被迫接受矿工们提出的16条要求。
1929年6月,混入工会的特务告密,纪子瑞被捕,押于山东省高等法院第一监狱。1931年4月5日凌晨,国民党省主席韩复榘以“供认加入共匪,意图颠覆国民党政府,阴谋暴动”的罪名,将邓恩铭、郭隆真、纪子瑞等22名***员在济南侯家大院刑场杀害。[11]
纪子瑞组建秘密工会的时候,张福林被选为工会主席。枣庄矿区外工会[12]成立后,张福林也被选为负责人。1928年8月,张福林组织矿区工人罢工,要求资方承认外工会代表工人的合法地位、允许失业工人复工、发放积欠工资并救济失业工人。资方多次派人收买张福林,让他别管众人的事,许诺每月给他增加几块钱。张福林不答应。于是,资方派矿警队逮捕了以工人代表身份前去谈判的***员张福林、蒋福义、王文斌和郭长清。
张福林等人先后被关押在峄县看守所、泰安监狱、省看守所和省第一监狱。官方动用酷刑,追问他们与***的关系。他们一口咬定自己是吃不上饭的工人。最后,这几位***员均被判处有期徒刑,郭长清死在狱中。[13]
这条红色工会线索的前端是纪子瑞,中间是张福林,后边有田位东。在“保持***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网站”[14]中,新华社电讯稿介绍道:
“田位东,1906年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1928年1月,田位东加入中国***,同年5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交通员。”
“1931年3月,党组织派田位东到枣庄,在煤矿工人中秘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先后建立起了中共枣庄矿区工作委员会、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田位东担任书记。矿区斗争环境复杂险恶,为了更好地组织工人斗争,田位东经常下井挖煤,深入工人群众,向工人讲解革命道理,把大批矿工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党组织领导下,矿区工人队伍逐渐壮大,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开展了多次罢工斗争。
“1932年7月,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组织领导数千煤矿工人,以‘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取消包工制’为口号,进行了‘七月大罢工’,并准备进行武装暴动。由于工贼出卖,不幸被捕。资本家摆下筵席,想软化、收买他,但他不为所动,并揭露敌人的阴谋。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他威武不屈,坚守自己的信仰。1932年8月3日,在济南千佛山下,田位东英勇就义,年仅26岁。”
与田位东同时就义的还有他的副手,中共枣庄特区党委副书记郑乃序。
为工人争取政治权利是有生命危险的。这些***人,甘心让大众搭便车,为大众冒大险,不仅需要理想和信仰,还需要一套激励机制和相应组织。田位东有诗曰:“前进!前进!/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胜利就在明天!”表达了他的理想和信仰。张福林1928年被捕入狱,出狱后恢复组织关系,参加抗日,中共建政后出任枣庄市市长,展示了组织的作用和激励的机制。在组织的激励和理想的鼓舞下,政治精英们以较少的命,为大众换得较多的命,换得既值钱又值命的政治权利,***因此获得大众拥护,最终夺得天下。这是以小搏大的精彩故事。
由此也可以看出,工会不仅对工人有价值。从政党和政治的角度说,工会的价值更高,这关系到工人跟谁走,关系到天下得失。
六、党派的价值
有意思的是,不管赤色工会还是黄色工会,都不是工人自己闹起来的,而是外来的政治精英发动并组织的。马克思认为,农民分散落后,属于旧的生产方式,如同一麻袋土豆,缺乏组织,无力表达自己的利益,需要别人高高在上代表他们。工人阶级则不然。可是中国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工人和农民的行为差不多。
从理论上说,工人们集体劳动,利益高度一致,更无后顾之忧,组织成本应该低于农民。问题在于,比起资方和官府制造的凶险来,这点便利简直不值一提。
资方怕工人团结起来讨价还价,便要收买工人领袖,收买不成也要事后寻机解雇,软硬兼施,不惜勾结黑白两道根除后患。官方怕工人聚众闹事,更怕异己力量发展壮大。他们对付异己力量的传统策略是“首恶必办”,露头就打,关押甚至处决。这些我们都在枣庄看到了。
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官家主义”[15] 体制中,资方与官方往往相互勾连。北伐军到达枣庄之前,中兴煤矿的董事长是朱启钤——民国初年的交通总长、内务部总长,一度代理国务总理。先后担任董事长的还有徐世昌和黎元洪这两位总统级的大佬,董监事中有周自齐、赵尔巽等6位省长部长以上的高官,军阀张勋、倪嗣冲、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也是公司的大股东。北伐成功之后,钱新之担任总经理。这位金融界名流,一转身便出任南京政府的财政次长,近似现在的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在这种体制中,资本与权力私下结合,权贵们可以公私兼顾,公器私用,镇压工人特别方便。
总之,面对官商联盟,挑头者风险极大,自我牺牲的概率很高。无论在工人阶级的队伍里,还是在贫下中农的行列中,甘愿为大众牺牲的圣人总是罕见的。工农大众的常用策略是:首先,尽量不当出头鸟;其次,一旦有了带头的,穷人或胆大的愿意跟着闹,中农或胆小的更倾向于搭便车。于是,在资本-官家主义的格局中,工人的低成本组织优势被抵消,代表阶级利益的自发组织难以产生,自发产生的往往是地域或江湖色彩浓重的帮会。当然我们不能抱怨中国工人阶级软弱幼稚,实在是形势太复杂,对手太强大了。
这时候,***凸显了反对党的价值。外来者承担了挑头组建工会的高风险。这些外来者信奉一套清晰完整的社会历史理论,还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和激励机制,他们不在乎资方的解雇和小恩小惠,也有办法化解、承担和补偿官府追杀的风险。这是他们的专业。在较弱的程度上,帮会和其他党派组织也有类似作用,他们之间还可能彼此竞争、合作和模仿。
***发动工人闹腾起来后,资方和官方立刻反应过来,开始争当工人阶级的代表,以便控制工人运动。
中兴煤矿的资方成立了“惠工处”,以表示“自动惠工之决心,并避免直接冲突”[16],奈何惠工处既要听老板的,又要为工人谋福利,两边不讨好,最后被劳资双方轻视,“逐渐加以淘汰”。国民党也派人来整顿并组建工会,这个工会确实为工人争到了一些利益。中共方面骂他们是“黄色工会”,“骗人”,“挂羊头卖狗肉”17,虽说也有道理,但站在工人立场上看,代表权的竞争格局比独家垄断好,工人可以用脚投票,淘汰那些冒牌货。
总之,工会很值钱,秘密工会是各种工会的先驱,秘密工会更值钱。***承担了组建秘密工会的高风险,引起了代表权竞争,作为工会之母,这个反对党比各种工会的价值都要高。工人政治权利不足,正要仰仗他们带头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