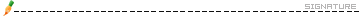九龄童不堪应试教育重负 从重点学校走入孟母堂
【来源: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周末】
孟母堂读经背后的故事
8月初,上海教育部门对私塾“孟母堂”举起黄牌,再次引发了舆论对“国学”的关注。本报对孟母堂进行了采访,而这次采访,最终将我们的关注引向了孟母堂的那些孩子们。
由于不堪应试教育的重负,放弃普通全日制教育,进入以诵读国学与西学经典为主的“孟母堂”,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选择有些无奈。
如果彻底全面的改革又不可能短期达成,那么施教一方可有温和有效的改善之策?
本次特别报道同时关注广州离休老教师郑千一的故事。她以国学为手段,在尊重现有教育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着人格教育的尝试,意图弥补学校教育的缺憾。
这两个故事都与国学有关,但我们无意借此进行价值层面的倡导。我们仅试图通过这两个事关国学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反观现时教育体制中有待提升之处。
本报记者 曹筠武
星期天的晚上,9岁的男孩朱季被父母送到了上海市郊的一幢别墅的院子门口。朱季第一个从车里钻出来,跳跃着进了门。别墅内正在晚餐,十多个和朱季年龄相仿的孩子围坐在两张长桌旁,纷纷起身跟朱季打着招呼。
别墅的主人,33岁的吕丽委坐在饭厅的门口,看着孩子们吃饭。13岁的男孩儿刘晨认真地舔掉碗里最后一粒米饭,双手把碗筷放进旁边桌上的大盆里,鞠躬后从吕丽委身边跑出饭厅,还不忘回头响亮地喊:大家请慢用。
吕丽委微笑着对刘晨投以赞许的目光,“孩子们很快就会学会我们的礼仪。”她说。
吕丽委今年33岁,曾经是厦门市一家模范中学的英语老师。而现在,她在这间别墅里指导十多个孩子诵读《论语》和莎士比亚,并在客厅中高高悬挂的孔子像下教授孩子们礼仪。
作为这个学习场所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吕丽委把这里命名为:孟母堂。
“找一个能轻松快乐的学校”
“一想到他还要这样上十多年的学,我就背上冒冷汗。”
在进入孟母堂之前,朱季是宁波一间重点小学的学生。朱季在那里读到二年级,他本来被期望和其他孩子拥有一样的学习和生活。
但父母很快发现,他们的孩子无法和其他孩子一样。朱季可能有一点多动症,喜欢跟人说话,爱把细细的胳膊挥来挥去,眨眼的频率比其他孩子稍微高一点。
在进入学校前,大家都善意地觉得,这个小孩儿,只是过于活泼好动了一些。但老师们不这么看。朱季的父母被频繁地召到学校,老师警告说,在学校,没有人管得住这个孩子。朱季会在课堂上说话,老师训斥他的时候,又觉得他在挤眉弄眼,没有虚心接受批评。
同学也瞧不起他“老是眨眼”,在学校,朱季没有什么朋友。回到家里,朱季的痛苦也没有结束。尽管才小学二年级,每天晚上朱季都要到9点10点才能做完作业。做作业的过程令父母看了心疼,8岁的孩子,被成语造句或者加减乘除折磨得焦躁不安,不停地挥着胳膊。
“一想到他还要这样上十多年的学,我就背上冒冷汗。”父亲朱宏回忆说。
朱宏找到老师,想跟老师“谈一谈素质教育”。朱宏觉得,小孩子不用特别精通四则运算,如果能够降低学习的激烈程度,再发展一下兴趣爱好,比如“琴棋书画”,孩子会健康一些。
老师很直白,也很无奈:“现在不是素质教育,现在比的就是做考题。”老师还很坦诚的告诉朱宏,作为一所著名重点小学的老师,他被分配的主要任务是抓好尖子生,而对于朱季这样的问题学生,“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管”,“只能看他的造化”。
“我感觉我的孩子被抛弃了。”如今说起来,朱宏仍然语调悲伤。
13岁的刘晨在学校也不快乐。这个高大而清秀的男孩曾就读于上海一所重点中学,“小学的时候他成绩很好的。”刘晨的母亲张丽说,“但是到了中学,好的学生太多了。”刘晨开始变得孤僻,不愿意跟母亲说话,一提到成绩,他就脸色铁青。“我甚至觉得,儿子对我越来越没感情了,有时候很伤心。”张丽说。
上个期末,刘晨的名次有进步,张丽试图夸奖儿子,希望借此能跟儿子有些交流。但刘晨突然狂暴地撕碎了卷子,嘴里不停地大叫,“狗屁的成绩,狗屁的成绩!”
张丽泪流满面,她觉得自己的孩子不能在学校呆下去了,“我承认我的孩子可能不如其他孩子那么会考试,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给那些孩子陪读,最后成为考试的牺牲品。”张丽决定给儿子“找一个能轻松快乐的学校”。
从“读经”到“孟母堂”
“我们需要有另外的更好的方法推广读经。”
在厦门做中学英语老师的时候,吕丽委就曾试图对教学方法做一些改进。她试图减少对语法的讲解,增加阅读量。但很快她又发现,这对考试成绩并没有太多好处,相反甚至还会降低学生的分数。
“我们学校是模范中学,成绩是最重要的。”吕丽委停止了她的尝试,“我明白,在既定的规范里,我个人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
她转而训练她的小侄子。她教5岁的侄子背诵唐诗宋词,甚至阅读《论语》。小家伙并不能全部记住那些音调多变的语句,但是一天在一个朋友家做客,5岁的孩子在被禁止触碰陶瓷茶具后,用叹气的语调吟出了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
吕丽委惊喜万分,她认为自己的训练终于显出了成效,“我觉得大量朗读和背诵经典,就是他说出诗句的原因。”
与此同时,吕丽委的丈夫周应之,一个熟稔金融资本运作的商人,也在经商之余发现了新的“人生乐趣”。
朋友推荐周应之阅读了台湾南怀瑾所著的《论语别裁》,并介绍周应之进入了“读经运动”圈子。“我受了很大的影响,发现了读经的好处。并且渐渐从乐趣上升成了人生的指引。”
同时周应之还发现了商机。他成立了“绍南”文化传播公司。“致力于推广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开始,周应之希望在厦门的中学中推广“读经”。他先印刷上万本儒家经典简读本,分发到厦门一些重点中学,包括妻子吕丽委所在的学校。然后再请老师为中学生们讲解。
但效果并不明显,中学生们兴趣明显不高。一次经过学校的垃圾站,吕丽委发现,被揉烂的儒家读本在垃圾堆里四处散落。
“我们需要有另外的更好的方法推广读经。”吕丽委说,“这个方法,不一定是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内的。”
去年7月,周应之和吕丽委来到上海,连同自己5岁的女儿在内,加上朋友的孩子,最开始总共教授4个学生。吕丽委负责指导孩子们背诵《论语》、《大学》、《易经》和莎士比亚。那就是“孟母堂”的开始。
“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个人品性的提升是我本来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从朋友那里,宁波的朱宏听说了“孟母堂”,他的想法是,“姑且一试吧”。此时他的孩子朱季已经陷入了对学校不可抑止的焦躁之中,他对孟母堂本没有兴趣,但当听说那里没有考试也没有作业,就不再表示反对。
在孟母堂,吕丽委拿给朱季一本《论语》读本,书里用汉语拼音标注了每一句话的发音。朱季胆怯又很好奇,周围的孩子都端坐在课桌旁大声朗读,在短暂的迟疑之后,朱季也开始照着读本朗读起来。
“在那个环境里面,小孩还是适应很快的。”朱宏说,“周围的小朋友怎么做,自己也会学着怎么做。”
按照孟母堂的课程设置,每天除早晨的跑步晨练和傍晚前的体育锻炼之外,上午和下午各两个小时读背是学习的主要内容。每个孩子有自己的读本,还有一台录音机用以播放标准朗读磁带。背诵的材料有《论语》、《大学》、《易经》、莎士比亚戏剧和包括马丁·路德·金著名演说在内的英文经典名篇。吕丽委规定,每篇课文,每天必须朗读80遍,并背诵一遍。但老师们很少解释这些深奥的语句。
“讲解并不是必要的。”吕丽委说,“重要的是在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把这些经典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自然会理解。”
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在孟母堂的地位并不高,孟母堂延请了上海一位老教师给孩子们教授数学,但只是“一周上两节课”。这位老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和孟母堂的文科学习一样带有大胆的想象色彩,他对小学适龄儿童们讲授从加减法到微分几何乃至拓扑学。
周应之对此有着比较个人色彩的解释,他认为孟母堂并非不重视自然科学,“我们学习《易经》,其实从易经里就可以发现包括所有自然科学的终极真理。”
当然,9岁的朱季并不能理解这种终极真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他至少可以在提供的课本中自由选择他喜欢的内容进行阅读,而不用像在小学,“一定要学讨厌的成语造句。”朱季习惯了在孟母堂每天晚上9点就上床睡觉。时间一到,他就往楼上宿舍跑。“晚上我不学习。”8月19日,他站在楼梯口说,“因为天一黑我的思想就睡着了,第二天再醒过来。”
对于其他孩子来说, 5岁的佳丽喜欢读《论语》,而10岁的小文居然喜欢“看上去很奇怪”的《易经》。13岁的刘晨比其他小朋友的英文程度更好一些。他更多地阅读了“英文名篇选读”。在包括了萧伯纳、丘吉尔、马丁·路德·金、肯尼迪等人的名篇中,他最喜欢柏拉图的《论正义》。他可以对照课本后附的汉语翻译弄懂这位先贤的思想。
孩子们同吃同住同学习,还一同欢天喜地地扫房间和庭院,尽管大多数时间需要勤杂阿姨重新打扫。老师要他们对每个同伴使用礼貌用语,对帮助自己的人鞠躬称谢,还要每天晚上开个小会,反思自己一天的不足,推举出今天表现最好的同伴。
身材高大的刘晨由此成为了孩子们尊敬的对象,因为他总是像个大哥一样在篮球场和游泳池照顾弟弟妹妹们。心情放松的刘晨,还开始主动和母亲沟通,周末回家前,他会先打个电话回家,询问家里有什么安排。“我第一次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高兴得快哭了。”张丽说,“他多久没主动跟我说话了!”在张丽眼里,刘晨越来越礼貌和富有责任感,“这在学校里不会教授也不会受重视。个人品性的提升是我本来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朱宏并不觉得自己年龄尚小的儿子在短时间内能学到多少东西,但他的确看到孩子脸上露出了越来越多的笑容。“我只能说,我的孩子的确不适应现行的教育体制。无论如何,在这里,他可以轻松一些、快乐一些。其他的以后再说。”
“我的孩子只能去孟母堂”
“至少现在,我的孩子,只有孟母堂可去。”
“我们认为,孟母堂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是不科学的,是不适宜儿童身心全面发展的。”在上海本地报纸于今年8月报道孟母堂之后,孟母堂所在的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对媒体公开表态说。
孟母堂的教学地点原本设在上海城区内桂林路一幢别墅内。在上海市食品监督局的检验员坚持要求进入孟母堂对学生伙食的卫生标准进行检测后,周应之把12个学生搬到了如今的城郊锦轩别墅区内。如今的别墅3楼,卧室内相当局促地摆放着七八张双层床。“我们这里都住不下了,只能让他们走读。”周应之说。
在开办初期,学生主要来源于周应之和吕丽委的朋友圈;在媒体报道之后,陆续有自寻上门者。按照吕丽委的说法,“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满身伤痕地从学校来到这里。他们只能是一小部分优秀学生的牺牲品,最后就成了我们现行高淘汰率教育选拔机制的残次品。”
8月初,松江区教育局下发通告,把“孟母堂”定性为非法办学,并要求周应之和吕丽委停止孟母堂的授课。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还向媒体表示,将在9月1日新学期开始之前,采取措施取缔孟母堂。
教育局的依据来源于义务教育法。一位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管理部门必须为每一个孩子接受合格与适合年龄阶段的教育负责,而有关部门经过调查,认为孟母堂并不能提供完整的科学的教育。例如,孟母堂几乎不讲授自然科学,所传授的社会科学知识,也与现代文明社会脱节。
但周应之认为,这种论断是“对传统文化无知的表现”。“我们中华民族依靠这些知识生存了几千年。”他说,“我们缺少的是从中吸取营养,而不是用所谓的现代文明来片面否定。”
然而,如何让孩子们在背诵“男女授受不亲”的同时,又理解“罗米欧与朱丽叶”?如何实践“君子讷于言而敏与行”,又学会向现代社会推销自己?或者,易经中的“上九,潜龙勿用”,又该运用在生活中的什么地方?
吕丽委仍然将这个问题抛给时间,她坚信时间的沉淀,会让孩子们建立融会贯通的世界观。
对于快满14岁的刘晨来说,现实的问题显得更加紧迫一些。与他同龄的孩子就要升入高中,高考、大学、择业即将接踵而来,刘晨的母亲张丽,不能不比其他小孩的父母考虑得更多一些。“今后应该还是要读高中。”张丽说,“我现在既高兴,又担忧。孟母堂不能发学历怎么办,对以后重新回到学校有多少实际帮助,这些我都还没想明白。”
朱季的父亲要宽心得多,他希望朱季能在孟母堂养成良好的品德和生活习惯,“大了之后再进学校,希望学起来能省力一些。”
周应之拒绝用任何带“学校”、“机构”的词语称呼孟母堂,他坚称,“孟母堂就是家长们联合自发举办的家庭教育。”对于绍南文化传播公司对于“孟母堂”式教学的推广计划,他也避而不谈。对于家长们每月缴纳的2000余元费用,周应之解释说,这是必要支出的平摊,不能认为是收费。
刘晨的母亲张丽还没有交费。刘晨加入的时间正是“取缔风波”时期,周应之对张丽说,先进来读着,“费用最后再说。”
张丽对孟母堂的老师们感觉非常好。她第一天来孟母堂,吕丽委热情地亲自下厨做了晚饭。“这里的老师让我感觉到尊重。”张丽说,“以前学校的老师,说实话看不起成绩不好的孩子的家长,总是呼来喝去。我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到尊重我的老师那里去学习。”
对于孟母堂课程的设置,张丽并不完全认同,“毕竟我的孩子已经大了,需要学知识。以后还是需要去上高中的。”但张丽并不愿对记者完全说明她的意见,“孟母堂总体对我儿子是有益的,其他问题可以慢慢协调。”
稍稍迟疑,张丽还是补充说,“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不像其他孩子一样考高中考大学找好工作,但至少他要健康快乐地长大,今后有份谋生的职业就可以。”
看着陪同孩子而来的家长们,周应之少有地对孟母堂的发展前景流露出了乐观,“看这些家长,这么不离不弃,孟母堂就一定有发展空间。”
张丽则一语道出了“不离不弃”的原因,“至少现在,我的孩子,只有孟母堂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