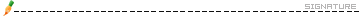杂记

我和妈妈、姐姐搬到外婆家隔壁去住。 那年我三、四岁,会说话、有记忆了吧。这一住直到姐姐小学毕业,而我也差一年就毕业了。
哪一年住进“间仔”我不清楚了,为什么叫“间仔”?因为它既不是平房更不是有厅有室的洋楼,是一间格子式的屋子,三舅就在这“间仔”里娶了舅妈,后来下乡回了农村,居委会号召养猪,就成了养猪的猪圈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不养猪了,好像堆放着杂物,收掉圈里的拉拉杂杂,就成了我们娘仨的栖息所在。印象中,“间仔”大概六平方米,地上的红砖经常被妈妈刷洗的净亮净亮,有的砖块一角红色已被洗刷成浅橘红色,但整个“间仔”就因为地砖的颜色很红,没有其它的颜色可跟它斗艳媲美,更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抢眼,所以我把它称做“小红砖屋”。也更因为在这小小的“屋子”里,有妈妈,有姐姐,有家的感觉。
小红砖屋的门是一个小柴门不足一米宽,是用几条长形的木板块组合成的,颜色枣红,毫无生气,白天门逢透光,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姑娘盼不到“出阁”似的无精打采靠在墙壁边。哪天才能见到生机蓬勃的朝阳?她也不知道。
屋子里还有什么,我也记不清了,记忆里依稀还见到朱红色的漆块斑斑点点地附着在椅子上,那是舅舅家扔掉的椅子,实木的,外婆找了几颗铁钉子把椅子加固修了一下便拿来给我们母女仨用,是整个小红砖屋最贵气值钱的家具。椅子旁边架着一条竹梯,梯子的另外一头直通到半吊小阁楼,挂着,冬凉夏暖的我们就在阁楼上睡了,那是我童年遥远而又炽热的梦。梯子边是个小灶台,放着一个蜂窝炉,那是利用舅舅家的滴水巷的巷尾搭起来的临时灶台,下雨天,炉子是无法生火的,漏水很厉害,“没办法,临时搭建的只能如此,”妈妈说。
灶台旁放着一口大水缸,用来蓄水的。一排排蜂窝煤叠放四五层,那些黑色的蜂窝煤特别的黑,泛着光泽,我后来曾经纳闷,为什么那些蜂窝煤黑得发亮?为什么我家小屋那对太师椅不是和舅舅和邻居家的椅子一样的红一样的亮?舅舅家的椅子很大,听妈妈说,那不叫椅子,叫“炕床”,用一种名贵的酸枝实木和大理石做的,上面还雕有梅花,鸟,石头等图案,花了大价钱买的,显得气派,听说这在以前只有大户人家或做官的家里才有,夏天的时候,人往炕上一坐,很凉爽很舒服。
蜂窝煤用木板装,二十个一板,一把火炭钳子经常伴着,煮饭时,要把炉子的火旺起来,必须用火炭钳夹一两个蜂窝煤放进炉子。记得有一次,我那双塑料鞋有好几根带子断了,脚趾都露出鞋外,还经常蹭到地,可妈妈不答应给我买新的,那时实在是穷,于是,乘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偷偷的学妈妈把火炭钳放进炉子里加热,待烧得钳子通红的时候,踮起脚,一手拿鞋子,一手拿火炭钳,可是那钳子好重,一只手拿不起来,只能又拖又提的,待钳子离开炉子时,便使劲提了起来,心想着要快点,钳子就快要掉了,又热又重的,狠一狠心,咬紧牙对准塑料鞋带的断口处,我使劲一捂,“呀,好疼,”我忍不住疼得叫出声,钳子直接捂到拿鞋子的食指去了,一阵灼痛直烧到心里,泪水止不住地流,“哐啷”一声,火炭钳掉到了地上,鞋带没补成,倒把手弄伤了,留下了一条像蚯蚓一样大小的疤痕。
平时妈妈启炉子,都要找些柴皮抽(木皮削)引火,上下加火才能把炉子弄旺起来。因为那时候我和姐姐都还小,炉子启火要讲究点技巧,只妈妈会,妈妈很能干,没一会功夫就把炉子弄旺起来。炉子在我们家最大的作用是用来烧开水和热水,开水是家里必不可少的,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生命之水。冬天来临了,烧热水洗澡就不用受冻着凉了,但洗澡的地方我们是没有的,每当这个时候,我和姐姐都经常要去跟舅妈商量,哀求舅妈允许我们借用她家的厕所,征得她的同意才可以去洗澡,当然,遇到要便便的时候,为了尽量不去看舅妈的脸色,我们通常是偷偷溜去上厕所的。
注:这篇杂记是简初次尝试学写,朋友们若有余暇时间请多多的给予指导指正。谢谢你们!
简
2009年4月18日凌晨记
哪一年住进“间仔”我不清楚了,为什么叫“间仔”?因为它既不是平房更不是有厅有室的洋楼,是一间格子式的屋子,三舅就在这“间仔”里娶了舅妈,后来下乡回了农村,居委会号召养猪,就成了养猪的猪圈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不养猪了,好像堆放着杂物,收掉圈里的拉拉杂杂,就成了我们娘仨的栖息所在。印象中,“间仔”大概六平方米,地上的红砖经常被妈妈刷洗的净亮净亮,有的砖块一角红色已被洗刷成浅橘红色,但整个“间仔”就因为地砖的颜色很红,没有其它的颜色可跟它斗艳媲美,更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抢眼,所以我把它称做“小红砖屋”。也更因为在这小小的“屋子”里,有妈妈,有姐姐,有家的感觉。
小红砖屋的门是一个小柴门不足一米宽,是用几条长形的木板块组合成的,颜色枣红,毫无生气,白天门逢透光,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姑娘盼不到“出阁”似的无精打采靠在墙壁边。哪天才能见到生机蓬勃的朝阳?她也不知道。
屋子里还有什么,我也记不清了,记忆里依稀还见到朱红色的漆块斑斑点点地附着在椅子上,那是舅舅家扔掉的椅子,实木的,外婆找了几颗铁钉子把椅子加固修了一下便拿来给我们母女仨用,是整个小红砖屋最贵气值钱的家具。椅子旁边架着一条竹梯,梯子的另外一头直通到半吊小阁楼,挂着,冬凉夏暖的我们就在阁楼上睡了,那是我童年遥远而又炽热的梦。梯子边是个小灶台,放着一个蜂窝炉,那是利用舅舅家的滴水巷的巷尾搭起来的临时灶台,下雨天,炉子是无法生火的,漏水很厉害,“没办法,临时搭建的只能如此,”妈妈说。
灶台旁放着一口大水缸,用来蓄水的。一排排蜂窝煤叠放四五层,那些黑色的蜂窝煤特别的黑,泛着光泽,我后来曾经纳闷,为什么那些蜂窝煤黑得发亮?为什么我家小屋那对太师椅不是和舅舅和邻居家的椅子一样的红一样的亮?舅舅家的椅子很大,听妈妈说,那不叫椅子,叫“炕床”,用一种名贵的酸枝实木和大理石做的,上面还雕有梅花,鸟,石头等图案,花了大价钱买的,显得气派,听说这在以前只有大户人家或做官的家里才有,夏天的时候,人往炕上一坐,很凉爽很舒服。
蜂窝煤用木板装,二十个一板,一把火炭钳子经常伴着,煮饭时,要把炉子的火旺起来,必须用火炭钳夹一两个蜂窝煤放进炉子。记得有一次,我那双塑料鞋有好几根带子断了,脚趾都露出鞋外,还经常蹭到地,可妈妈不答应给我买新的,那时实在是穷,于是,乘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偷偷的学妈妈把火炭钳放进炉子里加热,待烧得钳子通红的时候,踮起脚,一手拿鞋子,一手拿火炭钳,可是那钳子好重,一只手拿不起来,只能又拖又提的,待钳子离开炉子时,便使劲提了起来,心想着要快点,钳子就快要掉了,又热又重的,狠一狠心,咬紧牙对准塑料鞋带的断口处,我使劲一捂,“呀,好疼,”我忍不住疼得叫出声,钳子直接捂到拿鞋子的食指去了,一阵灼痛直烧到心里,泪水止不住地流,“哐啷”一声,火炭钳掉到了地上,鞋带没补成,倒把手弄伤了,留下了一条像蚯蚓一样大小的疤痕。
平时妈妈启炉子,都要找些柴皮抽(木皮削)引火,上下加火才能把炉子弄旺起来。因为那时候我和姐姐都还小,炉子启火要讲究点技巧,只妈妈会,妈妈很能干,没一会功夫就把炉子弄旺起来。炉子在我们家最大的作用是用来烧开水和热水,开水是家里必不可少的,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生命之水。冬天来临了,烧热水洗澡就不用受冻着凉了,但洗澡的地方我们是没有的,每当这个时候,我和姐姐都经常要去跟舅妈商量,哀求舅妈允许我们借用她家的厕所,征得她的同意才可以去洗澡,当然,遇到要便便的时候,为了尽量不去看舅妈的脸色,我们通常是偷偷溜去上厕所的。
注:这篇杂记是简初次尝试学写,朋友们若有余暇时间请多多的给予指导指正。谢谢你们!
简
2009年4月18日凌晨记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7-6 12:02:45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