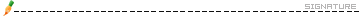焕展老师,一路走好!
作者:董建伟
虽然是暮春时节,可那个下午却特别灰暗,天边没有一丝云彩,空气中飘浮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阴郁。似乎一切都在冥冥中约好,善良而淳厚的焕展老师,在向人间作最后一次深情的回眸之后,悄悄地走了,永远地走了,并且离我们越去越远……
真是人生无常,不久前见到他时,还约好等他身体好了,就再到我工作的基层来走一趟,再写他想写而一直未写的东西。可如今是说走就走了,脚步何以这么匆忙!心痛、扼腕之际,想想,累了一辈子的老师,其实也是该好好休息了!
在汕头、乃至整个大潮汕的新闻界、文艺界,陈焕展都是一个令人心生敬意的名字;他倾毕生精力为地方新闻界、文艺界所做的贡献,有良知的人们都是不会忘记的;他留下的那几百万字被称为“潮汕平原新风俗画卷”的新闻、文学作品,至今也仍是一座令我们为之仰止的高山!
从当年上海街头一个叫卖洋葱的童工走来,陈焕展老师七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既亲历了旧社会的贫穷与黑暗,又领略过解放后的阳光和困惑。但不管生活中是苦是甜,是荣是辱,他始终怀揣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去烛照身边的一切;始终以一种真挚朴素的信念,去发现并诉说生活中的美好。仅仅因为读了冰心的《寄小读者》,便萌发想当作家的念头,十四五岁就开始给地方报刊投稿,居然经常被采用。解放前夕随家人从上海回到故乡汕头,不久便人伍成为一名记者。而后,历任《汕头日报》“韩江水”副刊编辑、文艺部主任、副总编辑,《汕头特区晚报》党组副书记、副总编辑、汕头作家协会主席。而从1948年开始写作以来,累计发表文学作品近300万字及大批新闻稿件,其中多篇作品获省市乃至全国奖,并入选各种选刊及读物。结集出版的有散文集《韩江拾翠》、《窗口的白云》、《阳光·草地》,报告文学集《乡恋》、《群星灿烂》、《潇洒走向前》等,也是粤东地区最早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两位会员之一(另一位为《绿竹村风云》作者王杏元),并历任广东省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四、五届理事,汕头市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委员。
从上面这段可以说是浓缩了他一生的简历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位在地方享有崇高声望的知名作家和报社老总!然而,人们对他的尊重,却并不仅仅因为他创作上的成就,抑或是他身处的职位,而更多是缘于他厚道朴实的人格、以及不遗余力发现和培养新人的无私精神。在当年,有数不清的作者,第一篇作品都是经他亲手修改润色后发表于《汕头日报》“韩江水”副刊上的,不少人还因此和他成了忘年交。尽管现实中他并不擅言辞,也不善交际,为人处事又总是那么低调、谦逊,但同时又是诚恳的、发自内心的,总给人一种亲切和真实的感觉。至今仍活跃在潮汕地区新闻界、文艺界的众多中坚尤其是青年作家,几乎都在不同程度受过他的影响和扶植,并且当中也有不少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像八十年代后才逐步成长起来的众多本土作家一样,我个人在文学创作乃至生活工作中,也一直备受陈焕展老师的栽培和关爱。记得当年那篇小说处女作《相亲的喜剧》,就是几经他耐心细致地点拨,而后几易其稿,才最终发表在《汕头日报》上的。也还记得,那时《汕头日报》还在饶平路,有一次他约我到报社去谈这篇稿子,刚好碰上单位的理发师傅为他理发,他就让我搬张凳子坐到他对面,然后他一边理发,一边跟我讨论怎样修改稿子,从小说的结构,到人物的塑造,从情节的发展,到语言的运用,他就那样由浅入深,像拉家常一样让我听懂弄清。后来这篇小说发表后,参加当年全省业余文艺创作比赛,还拿了个优秀奖!也是从那一刻起,文学像一抹灿亮的阳光,在瞬间点燃一个乡村青年全部的梦,并使我从此有了一份美丽的守望!也因着这份守望,深深地改变并影响了我此后的人生走向。
那时,家乡贫困且落后,全村仅有大队部订的一份《汕头日报》,而每次当我辗转拿到这份报纸时,不是被揉成皱巴巴一团,也是残破不全的。我只能把它小小心翼翼地抚平,然后躲在角落一个人悄悄地将就着读。那时,老师的名字就经常出现在报纸上,或是写新闻,或是写文学作品。及至后来,经过老师多少心血的浇灌,我自已的作品,也经常刊登在这张报纸上了,并在各种征文中频频获奖。可不久,我就离开家乡到远方谋生去了。但即便是在他乡,老师也一直保持和我书信往来,鼓励我在逆境中继续创作,才使我学会在别人的城市,仰望到工棚上空的点点星光。于是,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创作既成了一份令我难以割舍的牵挂,又像一盏温暖的小橘灯,照彻我生命中最伤痛的角落,使我在风雨中不致沉沦。
再后来,我回到了家乡,从机关的临时工做起,一边继续业余创作。这时,老师已是报社的领导了,也是刚成立的汕头作家协会主席。报社、作协担子两头挑,工作是更忙了,可这段时间,也是他创作最旺盛的季节,从《羊城晚报》到《人民日报》,从《作品》到《花城》,不时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洋洋洒洒,既有散文小说,又有特写杂文,并以其清新朴实、飘逸灵秀的风格,在岭南文坛独树一帜。在老师这种影响乃至催促下,这段时间我也勤奋地写了一批作品,散发在《作品》、《南方日报》、《散文》、《散文选刊》乃至《泰华日报》、《欧洲时报》等国内外报刊,但发得最多的还是在《汕头日报》的“韩江水”。像那时的《美丽的黄昏》、《乡村退伍兵》、《霏霏细雨》、《女儿河》等文,依然是我此刻心中最深情的眷恋。是啊,“韩江水”就像是一道清澈甘淳的源泉,在某一个早晨,抑或是傍晚,从我的生命深处流来,至今仍滋润着我的心灵和笔锋。
1987年,在焕展老师、韩萌(归侨老作家)老师等人的引荐下,我从潮阳侨办调到刚成立不久的《汕头特区晚报》任“龙泉”版文学编辑,从此开始我时至今日的职业文字生涯。时隔不久,老师也从《汕头日报》调到《汕头特区晚报》任职,传奇般地成了我直接的领导。此后在报社近距离的接触,使我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无论是工作还是做人,他总是那么一丝不苟,绝不敷衍。也无论是职务变迁,他依然像一位平和慈爱的长辈,从不摆架子。记得那时报社条件还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每天总是自己踩着自行车上下班,每次看着他踩车时有些歪斜的身躯,我总担心他会摔倒下来。在报社那么多年,我还从没发现他因为某些得失,而和人家吵架或较劲。他就一直以一种谦让、勤勉、自律的作风要求自己,从不做违背原则和损人的事;并总是以发现他人的优点和美德为乐事,而往往忽略现实中的阴暗和不快!
也许有人会说,他的为人处事太刻板,在生活中吃亏是少不了的。但我总想,以老师在创作上的睿智和灵气,他并不是不懂权术,并不是不懂圆滑,那些个中的利弊,他也应是了然于胸的,只是他不愿意、也不屑于那样做罢了!因为他的灵魂深处,与生俱来就是高昂着的。正是面对这样的一位老师兼领导,在当时的报社,我也从不曾仗着与他特殊的关系,而有所张扬或散懒,而是处处以老师当年做编辑时为榜样,默默而快乐地为“他人做嫁衣裳”,勤恳而认真地编好每一个版面,从而与同事一道把当时的“龙泉”版办得风生水起,在刚成立不久的汕头特区、乃至全国都产生广泛的影响,并同样培养了一大批本土作家。时至今日,“龙泉”版也依然是许多人心中一道美丽的彩虹。
与此同时,我继续坚持业余创作,并开始结集出书,还被破格评上中级职称。这过程,报社一些业绩平庸但其他不平庸的人,陆续被提为各个部门或版面的主任,老师心头肯定是有些想法的,但碍于我是他的门生而未敢坚持举荐我,或是根本就争不过人家。而我在当时其实也不太把这些当回事,只一心一意想当个好编辑、业余再写写东西就心满意足了,因而我也从不曾向他提过这方面的要求,并以此认为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九十年代中期,陈焕展老师从报社领导岗位上退休下来,本来辛苦了大半辈子,正是颐养天年的好时光。然而他却退而不休,因为依然担任着汕头作协主席,因为依然牵挂着地方的发展,他手中的笔,事实上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耕作。而不久,我也因着某种情结,又调回到基层工作。虽然见面少了,但联系却一直没有断过。也曾多次邀请他到基层来走走,他总是高兴地答应,可就是一年年拖着,一直到大前年才终于下了决心,让我开车带他下来走了一趟。记得那一次,我和致和老师(知名农民作家)一起陪他看了农家,看了工厂,看了周边一些风景,尽管那时他的身体己经不是很好,行动也有些迟缓,但他还是一路兴致勃勃,并从来没有过的谈笑风生,回去不久还写了篇观感寄给我,后来发在我主编的一本地方月刊上。
本来,他的晚年是完全可以过得更有情趣和清悠一些的。然而,这些年假如你曾去过他的家,你就会不难发现,在他那窄小的书桌上面,经常堆放着一叠叠稿子和书本,那是许多作者要出书请他作序,那是一些刚出版的新书要他写评论。还有一些社会活动,如 “潮汕星河奖”、“汕头文艺奖”、“潮剧基金会”等等,领导钦点要他这位“老将”担任评委乃至亲自撰文推介。可这些年来,他的身体一天天虚弱下来,各种杂病也接踵而至,只是一种长年养成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对这些“要求”不好推却,这便注定了他几乎每天都有忙碌不完的事情。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段,我想,他的心也仍在为没能完成某一件事、或是某一篇文稿而感到深深歉疚……
这就是为潮汕文坛许多人所熟悉、并发自内心深深敬重的陈焕展老师!
那天,送老师走的时候,我看到了,老师除了显得又瘦了,紧紧抿着的嘴角,依然是我们熟悉的神态,仿佛又在思考着什么;就是身上那套米黄色西装,也定然是我们曾经见过的,因为只有庄重的场合他才这样穿。摆满灵堂四周的花圈挽联,此刻就像一树树洁白的梅花,簇拥着悄悄睡着的老师。要不是小外孙女那足以穿越时空的哀伤低泣,谁也不会相信,你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要不是听着广东省作家协会发来的唁电,谁也不愿相信,此刻我们已然是阴阳两隔。那时,我多想伸出手去,可你分明已在另一个世界之巅。模糊中,我只看到一排排人,从你身边缓缓走过,向你作最后的道别。这其中,有特意从乡下赶来的农民作者,有工作在机关的文坛新秀,有现职或离职的市一级领导,更有许多曾与你朝夕相处过的老同事,每个人的心里,此刻要向你说的,都只有一句话:一路走好……
是的,一路走好,亲爱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