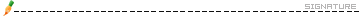黄自林:妈嫂
嫂子是村里娇小俊秀的妹子。我们弟妹几个和积劳成疾的爸妈是一张沉重的铁犁,只哥哥一个人拖着。嫂子却看上了我哥,要嫁到我们这个穷家来。村里人劝嫂子,说嫂子肯定会被累死的。
嫂子出嫁那天,她的哭嫁歌唱得又多又好,亲戚大多都被嫂子唱哭了。那时候二角钱一碗米粉,嫂子竟然挣了三十四元三角哭嫁利市钱。村里的哭嫁女没谁能挣到嫂子的一半。
嫂子嫁来的第三天就是九月开学。两个姐姐读初中,二哥三哥读小学。家里没钱也没值钱的东西,嫂子一分不留地拿出她的哭嫁钱,又拿出陪嫁的几匹的确良蓝布,为我们几个一人缝制了一套新衣裳。还差些钱不够,哥和嫂子就去担柴卖,我们几个也去,大大小小七个人排成一长溜儿,好多人替嫂子流泪,她是才过门三天的媳妇呀!妈妈哭哩,把嫂子搂在怀里,千言万语一句话:“我的宝宝哟。”
家乡湄河是一条养人的河。嫂子让我哥在河里捕鱼,她去圩上卖。清早晨雾未散,嫂子就在河边望我哥的竹排,夜里又挑一盏渔灯坐排尾为我哥壮胆。每当捕到一只值钱的鳖或一条河鳗,一家人都要高兴许久。嫂子出奇的倔强,明日分娩,今天还挑一担红薯苗上岭种红薯。嫂子虽累却没病,祖宗保佑我嫂子不会倒下。
没几年,多病的妈妈就去世了。村里有个习俗,在妈妈灵前焚一根竹筷,竹筷倒向谁,妈就最疼谁。我们一齐围着竹筷跪,结果竹筷旋了一圈儿后,倒向了嫂子。妈妈心里有杆秤,嫂子在妈妈心里的分量比谁都重。嫂子哭着向妈妈磕了无数个响头。那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
冬去春来一晃十年,姐姐和哥哥得益于嫂子也得益于苦难,上了中专、大学。嫂子的青春年华也为我们耗尽了。嫂子老了,我们长大了。
我们不知怎样称呼我们的嫂子。村里所有的嫂子没人能及我嫂子的零头。嫂子像妈像姐,嫂子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融合在一起,永远不可能分开。
姐姐从卫校毕业出来工作的那年,有一天,姐姐回来,一进门见嫂子的身影,就喊“妈――”嫂子回头看,姐姐才看清是嫂子。姐姐又喊的:“嫂――”在这瞬间,积聚在姐心头多年的情感如决堤的洪水倾泻而出,姐姐紧紧地搂住嫂子叫:“妈嫂――”姐姐一连叫了几声“妈嫂”。姐姐说:“妈嫂我毕业了,我工作了,就有钱了,您的苦日子也会到头了。”嫂子笑着哭了,说:“我知道的。”
现在我们一家是村里最幸福的一家。我们像敬重我们的父母一样敬重我们的嫂子。作为回报,我们会使才三十岁的嫂子不再受苦,我们保证。
村里人现在才说嫂子有眼力。嫂子说:“那时,尽管很饿,但他们是村里惟一不偷人家东西吃的一家人,他们和骨气贵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