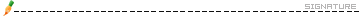一条狗的命运
谢娇兰
毛毛出现在家门口时,我们一屋子人正在客厅里赶手工,五弟的茶叶包装袋要赶赴昆明明早的班机。妈妈惊讶地叫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呀!毛毛怎呢回来了?”只见一条浑身脏兮兮的狗站在门槛外,惶恐而可怜的眼神扑闪着,赖以说明那不是一堆烂布,脏线团什么的。半月不见,它变得瘦骨嶙峋,蓬松洁白的软毛粘成一绺一绺的扫把条,是那种公共候车厅里被搁在一隅的扫把。它怯怯地伫立在门口,不敢近前半步,这个它曾经生活了两年的家,对它来说,已变得陌生而不真实。
半个月的时间恍若隔了几个世纪,它不知道回来的还是原来的自己吗?还是另外一条流浪狗?昨天的记忆依稀在脑:那时,它离开母腹才两个月,被一个中年男子用一只插花用的椭圆型竹篾花篮子,买了来。献给情人节的女人,以排遣她的寂寞。女人每天泡牛奶喂它,为它洗澡,喷用过期的兰蔻香水,或是鸦片香水。它是一条狗,当然不懂香水的名贵。但它却深谙主人对它的宠爱,它不知道在它身上寄托着女人对中年男子的爱念,它不懂。人与人间的感情已超越一条狗理解的范围。但它懂得主人的尊贵,因为被宠,也跟着尊贵起来,连坐也要跳上沙发,跟人一样像模像样,为它特备的花篮子本意是用来给它做床用的,男人在买下它时还细心地加买了一条柔软的大浴巾,供它暖身。那时是冬天,但它只把那当旅馆,是的,旅馆,它记得女人常对男人说起这个词,女人的被窝才是它的恬梦乡。女人也乐得边搂着它边睡觉,经常的时候是斜躺在被窝里,背靠床头屏,边跟男人通电话,边用尖细的涂了不同色指甲油的手指梳理它的毛发,痒痒的酥软,这种感觉就像女人电话里与男人的调情。
然而,万万没想到,短短才两个月,冬天还没结束,春天尚未来临。它的命运便来了转折,那时,它正伏在女人床的一角,像往日一样温驯地等待女人酥软的抚摸,没想女人却把它踹了一脚,重重地摔落在冷硬的地板。它听到女人对同样在床上的男人吼道,“你滚!离不了婚别再来找我。”它瞪大着双眼看这两个突然变得陌生的人,从没听过他们如此大声的吼叫,歇斯底里,它惶恐地看着这一切,仿佛骂的是自己,躲在一犄角,不知所措地等待着被人发落,就像做错了什么?但它又实在想不起自己错在哪里,女主人要用那样恶狠狠的一脚踹它。
它终于还是被带走了,连同那只花篮子。两个月,它才长出了一小截,稳在花篮子里才够一半空间,但似乎没有第一次被放进这只篮子时宽绰。黑暗中,它感觉到颠簸,两颗眼珠睁得像蓝宝石,总想看清它将被带往哪一个地方?好几次,它想站立起来,但颠感使它努力没有成功,当然还有害怕被呵斥的胆怯。
它终于被载到另一个家。女主人很陌生,凶巴巴的,小男孩倒是对它很友善,把他的“爱儿乐”撬开盖,泡给它喝,还蹲在旁边拿早餐的肉脯喂它。它好害怕,不知里面是否放了毒,一直不敢吃,似乎身子还在发抖。不知因为路上受凉还是害怕。男孩终于觉得无趣而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听到男人起床的声响。它迅即从竹篮里立起身,拚命向他摆尾巴,就像遇难的船只扬旗求援,除了他,它已没有感到令它放心的亲人了。尽管在前任女人那里时,狗眼里,男人永远只是个客人,每次来,欢迎的热情都不足三分钟,旋即又回到女人怀抱。但在此际,它却调动了所有欢迎的最高热情,以博男主人关注。早餐后,男人与女人商量了一会儿,它听出那话的口吻,没有与前任女主人那样温软,甚至很生硬。男人拽起竹篮便走,它只感到有电梯腾空而起的晕眩感,门“咣”的又关上了。男人顺手把早餐吃剩的面包屑撒在篮里喂它吃。
之后男人开始打电话。
在男人上班的途中,它又被送到了另一人家。从朋友手中接过这条狗,我的小孩可高兴了。那时,她正放假,独孩化无玩伴是我最头痛的问题,听说朋友新买了一条狗,因家里不让饲养,想转送人。我立马应承了下来。刚好给女人做伴。
小狗的样子很可爱,胖敦敦的,浑身白而柔软的毛发。女儿觉得好玩,说它像一条毛毛虫,但叫毛毛虫,我嫌毛毛虫太恶心,干脆去掉后面的字,叫“毛毛”。不久,这名字便成了狗的名号,每唤必应声而来,摇头摆脑的,煞是可爱。
毛毛与女儿成了玩伴,也成了女人的小尾巴。走到哪跟到那,有时叼走她的小玩具,有时跳在她作业本上印梅花。每次出门回来,毛毛热烈欢迎的激动程度几乎可说屁滚尿流。那是毛毛最开心,最本真的一段日子。可以不必为迎合主人而看人眼色,小孩子从不过分拿捏、刁难它。
遗憾的是这样的日子仅仅一个寒假。因为女儿要上学,怕她分神,我决定把毛毛寄养在父母家。双亲都退休了,日子闲着,养条狗又可看家又可作无聊时的玩物,更重要的是,女儿还可常常去看它,不会因为难以割舍而哭闹不已。
妈妈喜爱小动物,又心痛外孙女,对毛毛自是很爱护,从不饿着冻着,还时时为它洗澡,抓跳蚤。很快,毛毛便跟妈妈熟络起来。妈拖地,它便咬住拖把一推一拉;妈上市,它总在送出很远才跑回。妈妈果真把它当不会说话的朋友看。一晃便一年多过去了,毛毛从小狗变成大狗,尽官它的样子依然小巧。
毛毛开始发情了,不时有不知哪里的来公狗一到半夜就来门外叫敖,毛毛反应极其灵敏地冲向厅门,搔着嗯唧着,要主人开门。妈妈总是很人性化地起来为它解困。不久,毛毛便怀上了孕,拖着凸胖的肚像一条吞下超体积动物躯体的蜥蜴,显得笨拙而疲乏。浑身的毛也开始变脆变硬。四个月后,毛毛一口气生下了五胎,只只胖乎可爱,只有毛毛消瘦了。生了葸的毛毛耳不聪眼不明,不时干些捣蛋、破坏的事情,好几次把妈的袜子叼出去撕掉。主人外出回家,它辨别足音的灵敏性也锐减,几次吠错了人。让爸妈大为光火。尽管后来渐渐恢复过来。但爸妈养狗的兴趣似乎已被那一群狗葸子吵闹过程耗尽。每天闲不住,反倒成其奴役。终于在所有的狗葸断乳不久后,纷纷送人。最后就剩下毛毛送不出去。再说,养熟了也难以割舍。
放弃的念头策划了几次,终因下不了决心搁淡。恰巧有一天,家里来了乡下亲戚,把这件事跟他说了,他自告奋勇:回家时顺路把毛毛丢了。事已至此,也就由着他了。
为了安慰我们的不忍,亲戚过后回电话说,狗是丢了,但丢在一个人气很多的农贸市场边,不用担心它变流浪狗饿死。
如此一去,便半个月。正当我们渐渐忘了这件事时,它竟然就出现在家门口。